最新要闻
转载|父子参情深几许
发布时间:2025-07-15
许允平 许明良父子
七月的风,像一支饱蘸光阴的笔,又一次拂过长白山连绵至天际的参棚。林深处,几株历经三十余个寒暑的老山参,悄然在枝头攒聚出一簇簇细密的参果,沉甸甸,汇聚着山的魂魄,地的精元,以及时光的许诺。
许明良站在父亲留给他的1500亩参棚之下,目光所及,是无垠翻涌的绿浪。这片曾耗尽父亲全部生命的苍莽林海,如今早已化作托举他事业最厚重、最坚实的根基。
暮色四合,温柔地将群山拥揽入怀。那些浸染着父亲遗志的翠绿参果,在渐暗的天光里微微摇曳。许明良凝望着这片繁华景象,一股深沉的感动,甚至是感激,自心底悄然滋长、升腾。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点开那个无比熟悉的头像,在对话框里敲下:
“爸,看到了吗?今年参籽结得特别好……”
他的指尖微顿,更深的情绪涌上心头,于是忍不住又添上一句:
“爸,我想你了……我……特别舍不得你……”
(一)浙南中医世家的百年夙愿
许明良出生于温州市苍南县的中医世家。祖上至少四代业医,并兼修家传拳法。其曾祖父是民国年间浙南一带声名远播的郎中。
苍南医者对于长白山人参的深深渴念,由来已久。历经明清至民国,苍南县灵溪镇街巷间已是药铺林立,然而,那生于东北雪峰之下、可吊住人的性命的“神草”——长白山人参,却仍困于千里关山,难渡江南。这份求之不得的执念,在苍南医者的心头萦绕了数百年,许家自然深植其中。
当年,许明良的曾祖父开药方时,若遇重症,常会凝眉顿笔,带着无限惋惜道:“此症最需一味长白山老山参入药……”
这声沉重的叹息落入悠悠光阴,渐渐凝成了困扰许家后续三代人的一个心结。

许明良的父亲许允平,身高一米八零,身板挺直,脊背如松,天生一副习武的结实筋骨——这在身形普遍不算高大的苍南人中,堪称罕见。当青年许允平承继祖上的医术与拳法时,已有不畏艰险的苍南参商辗转千里,将极为稀少珍贵的长白山人参从东北贩运至浙南。
这些承载着关东灵气的人参经苍南转运,深入浙闽。参贩们常常行走在街巷之间,专门叩访沿海富户以及茶园主人。他们会小心地从怀中取出层层仔细包裹的布包或纸包,压低声音神秘探问:“您要人参么?正宗长白山的!”浙闽一带素重滋补,闻听是东北长白山所出,大多会即刻将人引入内室详谈。议定价钱后,参贩便会从整枝参上仔细切下几片薄薄的参片,如同交付珍宝般递给买家。
对长白山人参的这份深植于血脉的痴迷,加上强健的体魄与过人的胆识,让年轻的许允平毅然只身闯入长白山区寻参、开拓资源渠道。短短数年间,他不仅成功将长白山人参持续运往苍南,更建立了稳定可靠的货源基础,甚至带动了越来越多的苍南乡亲北上东北开辟新的生路。凭借这番实绩与威望,许允平被推举为苍南县参茸药材同业公会会长。
八十年代中期,苍南县一套体面的房子不过八千元。而许允平,怀揣着远超此数的十三万元积蓄,再度北上,全力开拓那魂牵梦绕的人参贸易。
临行前夜,妻子为他缝制了一件特制马甲——内衬密密麻麻缀满大小暗袋。许允平将钞票捆扎齐整,一沓沓仔细填入各个口袋。为掩人耳目,又在马甲外罩上一件宽大的棉袄。
长途客车载着寥寥二十余位乘客,驶向冰封的东北。身怀巨款的许允平神经紧绷,一路几乎不敢吃喝。渴极难耐时,才用水润一润嘴唇。他唯恐频繁下车如厕惹人侧目,暴露了那件破棉袄下层层包裹的秘密。
(二)黄金万两的万良
大巴车在漫天飞雪中驶入抚松县客运站——一座墙体斑驳的砖瓦平房,窗玻璃凝着厚厚的冰花。站前空地上零星停着几辆漆色剥落的“老解放”卡车,车轮深陷积雪。老许裹紧棉袄,踩着没踝的深雪走向售票窗口,买下一张去万良镇的班车票。

这是一辆窗缝漏风的黄海DD650客车,车厢内没有任何供暖,铁皮座椅冻得粘手。老许抱紧藏钱的马甲蜷缩在角落。窗外是延绵的雪野与黑压压的原始林,红松枝桠被积雪压成弯弓,偶有受惊的狍子从林间窜过,蹄印转瞬被风雪吞没。
班车在距万良镇3公里的大方村停靠——这个依山而建的小村落,仅有二十余户参农散居。老许在此换乘一辆马爬犁。车夫甩动系着红布条的鞭子,三匹骡马喷着白气,项下铜铃在风雪中摇晃,木制爬犁在冻硬的土路上划出吱嘎声响。行至北山岔口,积雪深埋路面,骡马嘶鸣着止步不前。老许只得付钱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徒步前行。
暮色如墨倾泻,林间风声渐如饿狼嘶嚎,枝头积雪簌簌砸落。老许后背沁出冷汗,手指死死攥住衣领疾行,忽觉脚下一空,整个人跌进被雪掩盖的塔头甸子草坑。他踉跄爬起,立刻摸向胸前马甲,确定钞票硬块还在,才抖落满身雪沫继续赶路。
不知走了多久,当双腿冻得麻木时,老许终于望见远处山坳亮起零星的灯火。万良镇的轮廓在暮色中显现。这片攥一把黑土能渗出油的沃野,正是他跨越三千里路途所追寻的人参产业的源头。
万良镇,静卧于吉林省抚松县东北15公里处的长白山西麓丘陵之间。若从云端俯瞰,这片土地宛如一株天成的老山参:松花江支流如参须蜿蜒伸展,镇中心台地隆起为饱满的芦头,层叠山峦环抱成参体轮廓。其下是腐殖质积淀千年的黑土(pH值5.5-6.5),冷凉气候与115-120天的短暂无霜期,恰为人参生长织就了天然的绒毯。
这里的人参栽培史,可溯至1567年(明隆庆年间)的种参第一犁。清代封禁政策如锁,将民间采参禁锢于官衙批文之下;直至光绪年间开禁,参棚方如星火燎原。据《抚松县志》记载,其时人参年产量已达28万斤(约140吨)。这便是参乡的初代基业,“万良”之名从此与财富共生。
二十世纪初,万良镇已成为抚松人参的集散心脏。参农们将沾露的鲜参捆扎成捆,经牛车骡马驮运至此,再沿驿道辗转营口、大连港口。岸畔汽笛声里,“京帮”商号的紫檀算珠与“沪帮”的洋行汇票,将这些关东瑰宝送往南洋的锡罐、西洋的药铺。1989年左右万良镇30%干参经苍南转销港台,苍南则发展出人参切片、蜜渍等加工产业链,两地形成“北方出原料,南方精加工”的分工体系。
此刻,许允平正怀揣着十三万元巨款,即将在这片流淌着“黄金万两”的土地上,掀起命运的波澜。
(三)跨越3000里的北参南渡
多年的人参交易,让老许与万良参农老王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老王的泥坯房,成了老许在长白山的第二个家。
命运的转折始于一次市场洞察。几年前,老许发现日韩市场对透若蜜蜡、断面凝脂的大力参近乎狂热。同样的五年参,红参每斤不过百元,而工艺精湛的大力参却能卖出三倍高价。可当他向参农打听制法时,老把式们却把头摇得像只拨浪鼓。
老许骨子里的执拗被点燃了。他与老王在积雪未消的农家院里支起铁锅,找来一筐筐品相中等的五年参,开始了漫长的试验。
每一次试验失败,老许都会详细记录当时的水温、冷淬时长、干燥形式……泛黄的笔记本上,墨迹与汗渍、参汁与雪水斑驳交融。
试验进行到第二十七天,大力参初现雏形。老许马上将记录整理好:晾晒定皮,水温95℃,烫制时间为22分钟(主根稍软可弯折而不断),再以0℃冰水冷淬5分钟锁住熟化层,最后火炕烘干缓慢脱水6天……
遗憾的是,同样的操作流程,下一锅人参却加工失败。老许又连续试验了几天,才猛然醒悟:标准化生产必须征服原料的个性差异。
此后的两个月,他白天向老把式请教浆足、皮嫩、无疤无锈的选参秘诀,夜晚则按重量、直径、浆气饱满度将鲜参分级,针对每一等级微调工艺参数。寒冬的泥坯房里,铁锅蒸汽昼夜升腾,冰水桶结了又化,老许的双手冻疮密布,却始终紧握计时器与温度计。
老许的日记本中这样记录道 :第146天,我们终于成功了。
那天,老许掀开烘干室(一个专门用来烘干人参的火炕)门帘的刹那,阳光穿透水汽,五十支参如列阵的琉璃武士,通体澄澈如松脂。他小心切开一支,断面赫然呈现三重金环:外层半透明角质环(淀粉糊化层,厚0.5mm),中层蜜蜡色过渡带(皂苷富集区,泛金丝纹),中心一点浅黄生芯(活性组织保留,直径≤1mm)。这正是日韩客商认准的“三环透芯”——中国大力参的黄金标准!
从那天起,老王的院子里不断涌进前来参观和学习的老把式,老许也毫无保留地和大家交流大力参的加工工艺。
越来越多的苍南人随老许走进长白山,将这里高品质的红参、大力参、白干参运往苍南。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些勇闯长白山的参商,在苍南县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参茸专业交易市场,经营户发展到200多家,年成交额达10亿元,东北三省各类人参总数的 80%,经苍南参茸市场销往国内各地以及东南亚国家。而许允平作为苍南参茸市场的奠基人与行业领袖,以及苍南——长白山供应链的建设者,促成“北参南销”分工体系的重要贡献者,先后被推选为苍南县参茸市场商会会长、苍南县政协委员,继续通过商会领导、政协提案及跨区域产业整合,将苍南从“无参之地”塑造成全国参茸集散中心。
2000年,老许在抚松县万良镇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人参加工厂。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融入了这片黑土地——从最初惊诧于东北人空口嚼生葱、啖生蒜的豪迈,到如今自己也成了这般作派的践行者。他在参棚旁辟出两垄地,随手栽下大葱。每至新葱抽叶时,老许便背手踱进地头,拇指食指一捻掐断葱管,“咔嚓”一声脆响,辛辣汁液混着泥土清气在齿间迸开,活脱脱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东汉子。
(四)守参人的朝圣
二十年商海浮沉,老许的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那是苍南中医许氏四代人对“道地”二字的追求与执念。老许与人参打交道的日子越久,便对“道地”二字执念越深。长白山乃《名医别录》里记录的人参生长圣境,其腐殖土的微生物群落、针阔混交林透光率,直接决定人参皂苷含量——此为“道地性”的科学内核。许氏中医世家的血脉若能躬耕于此,亲手侍奉这些“百草之王”,才是真正兑现、履行家族世代相传的药学信仰。

那年初春,老许终于攥着承包合同站在长白山西麓的参场。他把上好的人参籽小心播散在土里。为守好这点命根子,他卷起铺盖住进守参人的松木更房。
让人没想到的是,刚刚露出嫩芽的人参苗正处于一生中最娇贵和脆弱的时刻,长白山的气温却骤然降低,这场“倒春寒”几乎让老许的参娃子损失殆尽。
所有人都劝老许不要再种参了,虽然他和人参打了二十年的交道,但对于种参来说,他知道的仅仅是个皮毛。老许不听劝,像着了魔一样,仍然坚持在参地里摸爬滚打,用人参贸易的流水来填补种植业的窟窿。
一次,连续暴雨,老许的参须在浸水后发褐溃烂,老许半年的心血再一次化作腐土里的缕缕脓黄。这一次,老许对人参怕涝的习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所以,在之后的年岁里,他的参床旁永远有一条又深又顺畅的排水沟,他每天巡逻不让排水沟里有一片落叶。
一年夏天,万良镇遭遇了多年不遇的伏旱天气,宽大的阔叶,以及遮阳的参帘仍挡不住当空的烈日。参床被曝晒两日之后,参叶便蜷如炙烤过的蝉翼,人参的主根也渗出树胶般的汁液。老许再一次经历致命的打击。
那一年,老许拖着无比沉重的脚步,向长白山最深处走去。他在一片原始的针阔混交林中坐了下来,仰起头,望向天空。柞树擎起苍绿的华盖,椴木垂下婆娑的枝影,阳光透过针叶松如针般的缝隙洒落下来。老许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些无比珍贵的野山参为什么只长在长白山深处那些针阔混交林中。这是大自然最精密的布设:林间透光率掐在毫巅——多一分则参叶焦边,少一寸则参体羸弱。山风掠过榛丛与刺五加,将碎金般的阳光筛进腐殖层,恰够参根攒足元气,又不至灼伤纤弱的参体。他也终于想通了,为什么伺候了一辈子人参的老把式反复地训诫:“侍参如抚婴,三分在勤谨,七分靠天恩。”
后来,老许学会了用松针编帘遮阳,腐叶覆土保墒;懂得在暴雨前掘排水沟,旱季提山泉夜灌晨停。他似乎早已不再是一个在人参贸易流通中谋取利益的参商,而是一个对长白山、对自然草木生出敬畏的守参人,就像世代生活在山脚下的那些山民一样,他的心里长出了一种虔诚的信仰。
(五)为爱妥协
老许的参棚接连遭遇低温、暴雨和伏旱,许家苦心经营多年的参业几近崩盘。虽然,老许在妻儿面前,始终绷着那副磐石般的脊梁。但刚从浙江大学毕业便考入公务员队伍的许明良还是从父亲沉默的背影里读懂了他的千斤重压。他仍然记得父亲双手托举自己触摸苍南药铺“道地”匾额的温度,记得父亲当年扛着行李带着他穿越浙江大学报到处人海时的坚定。在许明良心中,父亲从来都是拓荒长白山的英雄,他豁达的笑容里永远藏着那份与天博弈的孤勇和追寻道地人参滚烫的梦想。

年轻的许明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公务员身份,研究长白山人参化妆品,和父亲并肩而战。
这是许氏父子最为艰难的日子。许明良的人参化妆品生意遇阻,老许却在种植人参并未看到明显回报的前提下,提出再承包1500亩参地的想法。
吉林人参产量占全国60%,世界总量40%,有着400多年的人参栽培史和文化积淀。而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于1989年正式建立,经过多年发展,2015–2016年通过国家级政策背书和市场规模优势,正式确立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家级人参交易专业市场,全国80%的人参在此交易,早已成为世界人参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地处这样的“人参之乡”,货源数量、质量都很稳定,又何必亲自种参呢?而且大面积种参,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风险又大,最重要的是父亲的年纪不小了,一个人在东北,许明良不放心,所以许明良态度很坚决,他不同意患有糖尿病的父亲扩大种植规模,再为种参的事过度操劳。
父子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许明良见父亲此意已决,再无回旋余地,只好妥协,通知公司财务,紧急给老许划拨了承包款项。
老许的新参地在长白山脉深处,举目皆是莽林。没有电,入夜后黑暗便立刻吞没山脊;没有自来水,饮水需翻过两道坡坎去背山涧溪水。参畦间鼠穴星罗棋布——这些贪婪的小兽嗜食参根,在腐殖土下掘出纵横暗道。鼠患泛滥处,蛇影便如幽灵般纠缠不休。老许的火炕是蛇最喜欢的地方。有时候,老许在参地里干了一天活儿,回到更房时,炕上正盘着两条蛇。有时候,他正睡得香,突然感觉胳膊一阵发凉,一条黑蛇正爬过他的身体。有时候,蛇就倒挂在他的房梁上……人与蛇的疆界在此消弭,蛇群俨然成了这苦寒之地的第二主人。
山峦如墨,将许明良和父亲阻隔成两座孤岛。许明良指尖悬在手机通讯录“父亲”二字上,像悬着一颗不敢落地的心。无奈,长白山的信号比人参精还飘忽,那些无法接通的忙音像一根根冰锥,扎得他深夜在办公室里踱步。父亲血糖仪的数值、火炕上盘踞的蛇影、参棚外三十年未遇的酷暑……所有恐惧在忙音里发酵成黑压压的云,沉沉压住他每一次呼吸。
有时父亲的电话也会奇迹般接通,父亲喘着粗气的声音裹着山风撞进许明良的耳朵:“刚跑上东坡…这儿信号稳!”许明良喉头一哽,眼前浮现七十二岁的背影在陡坡上蹒跚攀登,枯瘦的手高举手机如同举着烽火,只为给儿子点一盏虚无的平安灯。
(六)以命相守
2017年7月,三十年未遇的酷热炙烤着参棚。一株老参的叶尖泛起病态的枯黄,叶片卷曲垂向泥土,像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老许伸出皲裂的指腹轻触叶脉,仿佛诊脉的老中医,全然忘记自己的血糖值早已飙过警戒线。
老许的汗珠从沟壑纵横的额角滚落,砸进腐殖土时发出松针折断般的细响,竟比他擂鼓般的心跳更清晰。儿子捎来的胰岛素堆叠如未拆封的家书,可他的目光始终锁在那株叶尖泛黄的老参上。蔫垂的叶片蜷曲如婴儿的拳,攥着他最后的心力。

千里之外的广州,许明良总是突然地心慌。这感觉如影随形,像山雾裹住参棚般缠上他的四肢百骸。
老许的胰岛素消耗得越来越快,许明良托人送药的频率从旬日一趟增至三日一程。父子俩的通话从每日一次变成早晚两次。直到那日,老许终是松了口:“等参下了山……我就回苍南。”
无人知晓,这究竟是老许掏心掏肺的承诺,还是搪塞儿子的权宜之计。
可命运的镰刀来得比参叶泛金更快——老许终究没能等到人参下山的日子。
那日,长白山罕见地沉默着,毒日头高悬如熔化的金球,热浪舔舐着参棚的草帘,蒸得腐殖土腾起青烟。老许跪在参床边凝望那株重焕生机的老参。经他昼夜侍奉,原本蔫垂的茎叶已挺立如戟,露珠在叶脉间滚动,像含着未落的眼泪。
就是这个中午,老许永远倒在了他亲手救活的老参旁,倒在这片吞下他三十年光阴的土地上。
参叶簌簌颤动,水珠滚落在他骤然失温的身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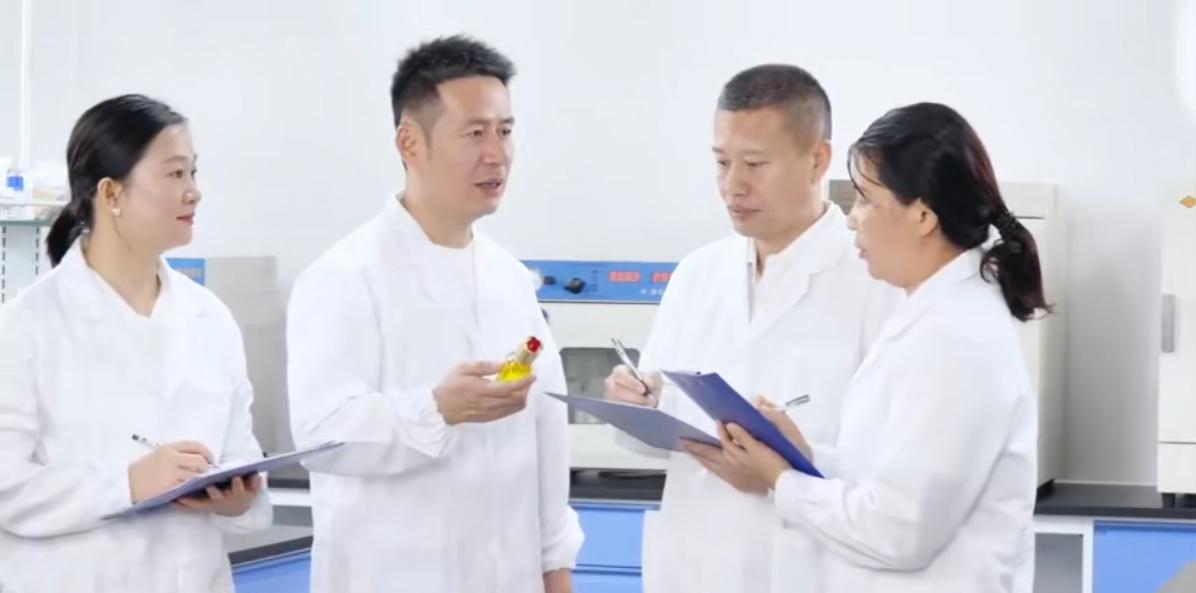
没有人知道老许是如何倒下的,是毫无痛苦地突然倒地,还是经历了各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他还有没有想和儿子说的话,或者想留下什么重要的嘱托,毕竟他心心念念的长白山人参就要下山了啊!
噩耗,翻山越岭,摧心的力量却丝毫没有半分削减。它像一剂重拳,狠狠打在许明良的心上。他的心脏似乎骤然停了几秒。他冲进飞往长白山的客机时,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
三万英尺的高空,机翼劈开层叠的云峦,舷窗外雪浪奔涌如长白山的冬雾,那些关于父亲的记忆或是憧憬,被一阵阵剧痛猛然撕开了口子:
那日秋风吹过参棚,父亲开着拖拉机带他巡山。引擎震颤着山坳的寂静,车斗在泥路上颠簸如舟。父亲指着一望无垠的参棚告诉他,那些参床深处埋着上万株三年生的人参。
车头拐进林子深处。父亲猛得刹住车,拨开密集的藤蔓与杂草,告诉他,那林下藏着上一任参场主三十年前用老籽播落的林下参,这些老伙计被霜雪啃过,野猪拱过,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许明良循着父亲的手示望去,在那腐叶间,偶现朱红的参籽如星火灼灼。
许明良偷偷举起手机,自拍了一张与父亲的合影。那一张合影,他在前,父亲在后,两父子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也就是那一天,父亲亲口答应他,只要人参下山,就和他一起回家。
可是现在,父亲永远也无法回家了。他倒在了那么遥远的深山里,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只有那漫山的、不会言说的人参。
(七)爱的回响
温州苍南。
父亲的房间,还保持着老样子。许明良每次回家都会一个人静静地在父亲的房间里坐一会。
父亲在墙上的照片里微笑,身后是一大片参棚,参棚里红色的参果像一团团热烈的火。许明良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父亲的所有照片,只有两类,一类是与家人的合影,一类是与人参的合影。而他与人参合影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家人。那些父亲与人参的合影里,他挂在脸上的笑和来自内心深处的幸福和满足,竟然穿透了相纸,穿过了岁月,直抵许明良的心。

“爸爸,你到底有多爱你的那片参地啊!”许明良在心里反问这句话时,眼泪一下子涌满了眼眶。
老许仍在照片里笑着,不做任何答复。
在一个满满当当的抽屉里,许明良找到了父亲留给他的答案。
那抽屉,是整整齐齐的,里面是三十多年来,老许往返苍南与万良的车票、机票,是参地的承包合同,用工票据,是人参种植技术学习笔记,以及一个中医世家传承人对“道地”药材的理解和坚守。
许明良静静地翻着父亲的抽屉,好像回到了自己很小的时候,父亲慈爱地拉着他的小手,给他讲自己的一切,讲他是如何从仓南走到抚松万良,讲他与那些人参的过往。原来,它们之于父亲,早已不再是牟利的手段,也不仅仅是药材,也不仅仅是夙愿,它们对父亲的现实意义已经越来越模糊,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和父亲的三个儿子一样,得到了父亲全部的爱和呵护。
抽屉被轻轻关闭,许明良拨通了东北朋友的电话。父亲活着的时候,为了逼迫父亲下山养病,他曾联系朋友,让他帮忙把父亲的工厂转卖或者转租出去。然而,现在他反悔了,父亲留在山上的一切,都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要做得比从前更好,这是父亲永远的心愿,也是许明良的心愿。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许明良突然改变了主意,大家只知道,许明良是个孝子,而今,他决心扛下这份伤痛,沿着父亲的脚步继续前行,或许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吧。
8年,弹指一挥间。
当山风卷着捷报掠过参棚,许明良的人参籽油已经摘得国家发明专利,琥珀玻璃瓶盛着的参籽菁华油正随“长白山人参”地理标志的金色印章,涌向巴黎的化妆品专柜。漂亮的中国风包装,正向世界宣告着东方美学的回归——那盒盖开启时徐徐展露的野山参,恰似长白山在千年冻土中捧出的金色心脏。
抚松参乡的地平线上,他继承父亲遗志建造的人参文化小院已然矗立。青瓦小院里蒸腾着古法浸润的参香,博物馆展柜中陈列着从三国《吴普本草》到现代皂苷萃取技术的千年参脉。
许明良依靠着长白山老山参的信誉,在全国各地开了1300多家人参护肤品销售门店。各地代理商每有机会都要亲自来参地看一看,亲手挖一棵老山参。
而这一切,许明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看到啊!他多么希望那个永远挺拔的英雄一样的父亲,能够感到欣慰和自豪。
他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轻点“发送”,两行饱含重量的文字,连同那无声却汹涌的思念,倏地消失在寂静的虚空,它们穿过参茸的气息、穿过山风低回的呜咽,奋力穿越那阻隔了生死的、模糊了八载春秋的界河。
天幕拥揽着山峦,山峦偎依着天幕。许明良抬起头,满天的星光瞬间浸没了他的身影。此刻,他更加执拗地笃定:无论父亲身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存在,他一定能够感知——一个儿子向父亲发出的、永不抵达却始终在路上的——爱的回响。
(本文转载自:吉林日报彩练新闻,作者:孙翠翠)














